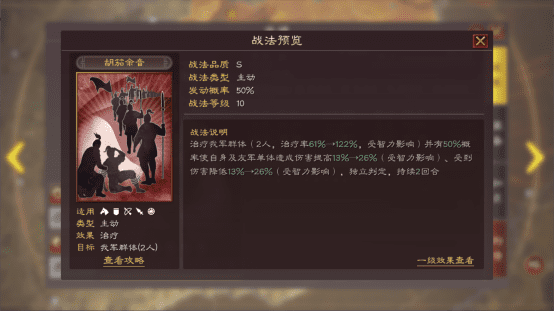一
唐开元年间,王沐为明州刺史。
王刺史性好雅静,偏爱仙佛。
公务之余,按月给自己排出日程:
上旬十天,清心寡欲以学道;中旬十天,沐浴焚香以参禅;末旬十天,喝酒吃肉养身体。
后院有十几亩地,刺史叫人把凡俗的花木、彩砌的亭台,能铲的全铲了,能拆的全拆了,所有带烟火气的东西都扔了。
锁上院门,撂荒了两年,直到它完全疯长成一个荒园,才教人用竹子在园中搭起一个三丈高的高台,名为“”招仙台,园子上又挂了个匾,叫“来仙园”。
从那以后,春秋两季,蚊子不多的时候,太守天天在竹台上过夜。
为了激励自己,冬天也咬着牙蹲过两宿,结果蹲出了重感冒和老寒腿,也就算了。
不为别的,就为了以示隐逸和高洁,等仙人来渡化和接引。
苦苦的支撑,勉强营业了一年,好像也没什么仙人光顾,倒是全天下成仙的奇闻异事灌了一耳朵:
谁谁谁入山访道不归,三十年后被樵夫发现在山涧下弈棋,容颜不改;
画工为道馆粉墙画仙箓图,偷偷添画自己肖像,遂成仙童;
谁谁谁家贫无粮,入山采柏叶为食,久之身轻体健,通体异香,被封“柏叶仙人”;
王老二家的大黄,叼给讨饭的乞丐一块干粮,结果被牵走了,只剩下一张皮;两个月后群仙下界,宝马香车,把王老二一家都接上了天;为首的一个长嘴的仙人,就是当初的大黄……
狗,狗都能成仙哪!
而且据家童说,王老二家就跟刺史的“来仙园”隔了一条街。
刺史大人很痛苦,幽幽清夜、扪心自问:
“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吗?
狗都能办到的事儿,我不行?
我这个“来仙园”,成功的将神仙们屏蔽了啊!
眼瞅着街坊家的狗都成了仙,大人我准备了这么多年都成不了,别人还以为我是故意的哪!
差哪儿呢?难道是……因为这院墙?
院墙太高,神仙爬不过来?”
拆!
一声令下,只用了半天时间,原来两丈高的墙砖院墙,拆得只剩下两米。
果然,当天晚上就有了情况。

二
刚过了中秋半个月,晚上蚊虫凶得很,露水又重,刺史叫人送来两床棉被。
不只为了御寒,院墙一拆,总有小孩儿淘气,隔墙往里打弹弓。
虽然夜色可以影响他们的准头,奈何月光皎洁,他又穿了一身白。
墙拆完了,不知效果如何啊?
刺史大人不避艰险,冒着绳命危险执意“坐台”。
更深露重,树影婆娑。
刺史大人端坐高台之上,围了棉被,堪堪将要睡……醒。
墙外突然有了琴瑟之音,异香扑鼻,直沁大人的心脾。
睁眼一看,矮墙之外,灯火通明。
两个童子提了水晶宫灯前导,后面跟了两排腰肢纤细的侍女,全用白纱遮面。
人人手提花篮,一路走,一路撒花瓣,黄的,白的,黄的,白的。
再往后是四个力士,肌肉虬结,戴了面具遮脸,肩抬着一乘云萝暖轿。
轿帘一挑,轿中正襟危坐一位仙娥,玉骨冰肌,绝代的姿容,朝高台之上略一招手,轻摇螓首、慢启朱唇:
“妾身本月宫姮娥,向慕使君寒素,道心颇坚,特乘月色来拜。
此园荒悖,妾于与瑶台设素斋一席,以结永好,使君可速随我去……”
刺史大人,心花怒放啊,这见效也太快了吧!
所以说,姿势不对必须起来重睡啊。
这个墙不拆,别说“招仙台、来仙园”,你就是把“唤仙、等仙、盼仙、催仙”的标签全标上,也没吊用……
拆个墙,仙人就来了啊!赶紧的,那还等个啥啊?
“隔墙疑是玉人来啊!”
大人风雅的吟哦着,爬下高台,跨过短墙,跟仙女走了。
三
过了……大概有三天吧,大人回来了。
披着棉被,倚在门口喘气,两眼放光,但是失魂落魄。
夫人赶紧命人给架到屋里,扶到床上,喂了两口热水,问他:
“疯哪儿去了你?三天哪……”
刺史大人一脸得意的样子:
“老爷我……我成仙了啊!”
夫人轻蔑的一笑:
“呦呵……那你怎么又回来了啊?”
刺史大人一脸的意犹未尽:
“你不知道啊……琼瑶仙宫,金堆玉砌啊,满坑满谷的月里仙娥、国色天香啊……老爷我被奉为上宾,劝酒的劝酒,喂菜的喂菜……”
“等等,”夫人的眉毛树了起来,“你说你去的是什么地方?”
刺史说:
“夫人,老爷我去的是仙宫……瑶台啊,那种地方,你永远也去不了啊!”
夫人杏眼圆睁:
“去尼玛的老爷,还瑶台?窑子吧!”
刺史很激动:
“休……休要胡说!老爷我乃是有仙缘的人……”
夫人更激动:
“胡说?我就问你,你后院的白玉香炉、赤金云磬呢?你的象牙笏板呢?你的碧玉簪青玉环白玉配呢?你手腕上的金手环、指头上的翡翠扳指呢?你腰上悬着的宝贝田黄印章呢?都哪儿去了啊?”
大人有些结巴:
“供……供奉了啊!仙人们说了,我这一身人间俗物,如果不捐弃了,难证正道,这么多年修来的仙缘将会前功尽弃、一切归零。开始我也还有些难舍,仙人说帮我来断舍离,来了四个力士,摁住我的手脚,把我剥了个干净,嘿,你别说诶,失去这些累赘,浑身一爽啊……”
“那叫浑身一爽?那叫浑身一凉好吧?然后呢?”
“然后……然后仙人说我灵根未固,还需再行历练,这次先作罢,下次……再来……”
“还特么有下次?
你特么这是碰上“仙人”啦?
你这是碰上“仙人跳”了好吧!”
自此,夫人命刺史大人闭门谢客,毕竟,太丢人了啊。

四
王刺史拆了的院墙,夫人又给重新垒了起来,还在最上边粘上了铁蒺藜和碎瓷片。
再有“仙人”敢铤而走险,极有可能会被扎了屁股。
保险起见,挨着墙根儿,还下了两层老鼠夹子。
老鼠夹子再往里,夫人又叫人挖了一条壕沟,深达一丈,不管谁掉下去都能修成“铁拐李”。
园门上“来仙园”的匾额,高高的还在,但园子已经被夫人布置成了“诛仙阵”,外防“仙人”,内防老爷。
刺史大人本尊,也被“监视居住”了。为了帮大人厘清修仙和奇遇的关系,夫人特意安排了自己的四位近侍,来负责料理老爷在内宅的饮食起居。
这“梅兰竹菊”四位姥姥,本是夫人的妈妈的陪嫁丫头,又成了夫人的陪嫁丫头……
这四位骨灰级的“梅香”,整得老爷心如死灰、古井不波,渐渐的对红尘俗世没了一丝留恋。
大人天天念叨着“向死而生”,琢磨着到底该怎么“尸解成仙”,及早离了这没滋没味的俗世。
是图好看用白绫子呢?还是整高端的直接吞金呢?
正纠结呢,有人来报,说定州大老爷家的二公子来拜。
五
刺史大人一下来了精神。
本家的亲侄子来了,这个“客”,夫人那儿没理由再谢了吧?
而且,这个大哥家的二小子王佐,跟他本人兴趣相投,也是个好道之人。
这真是思贤若渴,想睡觉老天爷给送枕头啊。
赶紧叫人请进来,叔侄二人一顿侃天侃地的寒暄,熟络得没大没小。
夫人见他们叔侄情笃,也就任由他们喝酒胡扯,自己回屋温习女德功课去了。
屏退了左右,王大人问他的侄子王佐:
“我侄子,最近功课怎么样啊!”
王佐回:
“小侄我蒙叔叔荫蔽,天子赐了进士出身,正候补呢……”
王刺史说:
“……废话废话,问你那个了吗?你那工作不是我给你安排的嘛,我不比你清楚啊?我是问那个……功课,那个……”
王佐说:
“嗨,我的亲爸爸诶,五叔,不就是仙道的事儿嘛,直说不就完了?怎么还藏着掖着的,跟逛窑……”
王刺史赶紧一把捂住他的嘴:
“嘿,小兔崽子,嘘!这种事现在不能声张,叫你五婶听见,我这月的餐标又得降……天天山药黄精熬成粥喂我,灵芝茯苓磨粉当茶灌我,还派了她陪送过来的那四只老怪物监视我,你看看我现在还有个人样儿吗?”
王佐偷乐:
“这不挺好吗五叔,你这清心寡欲的正和道家的无为之态嘛……话说那四位姥姥,我六岁的时候她们就这幅尊容吧,这一晃十多年也没个变化,驻颜有术啊。刚进来看她们亦步亦趋的跟着你,我还以为五叔你把她们给收了房哪……”
“胡说八道,胡说八道,”刺史大人拿筷子抽他侄子的嘴巴:
“小魂淡敢拿你叔叔开涮,别以为我疼你就舍不得打你……话说我再饥不择食也不至于打破生殖隔离吧,就那几块料,估计你五婶的爹我的老丈人,当初是当石狮子买回家镇宅的……再笑?再笑撕你的嘴,你小子别闲着,有什么奇遇给我讲讲,我这几个月不死不活的,都特么抑郁了,道心都不……坚了,赶紧给你叔叔来碗鸡汤吊吊命,快!”
王佐说:
“我的亲爸爸诶,我五婶把你迫害成什么了这是?我就没听说过拿鸡汤吊命的,不都是拿人参吊命吗?看来你这不是道心动了,你这是胃里的馋虫动了啊……”
刺史说:
“小魂淡,别扯淡,到底有没有……”
王佐说:
“……有倒是有,你不就想知道这世上是不是有真仙吗?我还真碰上一位,准确点说,是我以为自己还真碰上那么一位……”
刺史大人抿了一口酒:“说啊……”

六
王佐说:
“就是去年的事儿。
我不是得了进士出身,进京候补吗?
当然也没补上,到现在也没补上,补上了我今天也不会来找你啊五叔,也就没人给你讲故事了对吧?诶,对了,你该不是为了听故事才故意让我补不上官儿吧?五叔?那你就太麻辣隔壁了吧?……别打别打,长辈也不能总打人哈,接着讲接着讲……
回家的时候,路过杜陵,荒郊野外的,景色殊胜但四野无人。
白云变幻,野花自芳,满川的秋色,自生自灭,但是依旧生机盎然,实在是令人感慨啊……
哎呦……五叔你有病啊,讲故事不都得先抒抒情、写写景嘛,上来直接给高潮啊?那多不健康啊?你这是要喝鸡汤的架势嘛?我直接给你来个烤鸡架多放孜然怎么样啊?……别闹……马上就入正题了。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我把糕点带给外婆尝一尝……我去,我当然有糕点,我就不能有外婆吗?你再打人我可恼了啊!就没见过听众打说书先生的!
不是我说你,五叔,你在刺史任上这么多年也没个升迁,就是因为你文化水平……忒低。
文学!文学你懂吗?
上来就要干货,听有用的!我这不是公函,是文学!你明白吗五叔,文学就没有有用的知道了吧?
有什么区别?
就好比你吃豆沙包。
五婶正包豆沙包呢……是,我知道这娘们儿不会做饭,这是打比方哈。结果你忒猴急,上来直接挖了一勺豆馅吃了……这不叫文学。
什么叫文学。蒸熟了,摆上桌,你老人家拿过一个,小口小口地细嚼慢咽,仔细的品味,咂摸滋味,吃到豆馅的那一刻,甜……香……,这才叫文学。
什么叫高明的文学啊?你看刺史大人的觉悟就是不一样……这样啊,还是五婶做豆沙包哈。蒸熟了,摆上桌,你老人家还是拿过一个,小口小口地细嚼慢咽,仔细的品味,咂摸滋味,带着十二分对豆馅的期待,左一口右一口,兴致勃勃的吃完了……完了,居然没有馅儿,吃了个白馒头。这就是高明的文学。
诶,不许动手啊!五婶包豆沙包没馅儿也正常啊,她又没下过厨房……为啥会包出一个没馅儿的?一上来你不是挖了一勺豆馅儿吃嘛?哎呦……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哎呦,刺史打死人咯……”

七
王佐接着说:
“咱们言归正传啊。
我不是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吗?
虽然很窄,但还算官道,平坦坦的通向视野之外,一览无余。
路基往下,是满坡的野草,再下边是幽深的林子。
旷野无人,只有天籁相伴左右。
突然,右边的林子里,传来一串清脆的铜铃声。
一头瘦驴,驮着一个人,出了林子,沿着坡上的羊肠小道,噔噔噔噔的上到官道上。
小毛驴挺清秀,大眼睛水汪汪的,四个蹄子雪白雪白。
驴屁股上骑着个老头儿,胡子头发也是雪白雪白的,一张脸红扑扑、乐呵呵的。
斜挎着一个鹿皮口袋,除此之外也没什么行礼。
我觉得挺好玩,也挺稀奇。
这个老人年逾古稀,一副乐天知命的样子,独自郊行旷野……看那旁若无人怡然自得的架势,分明就像是绿野里的仙踪么。
我赶上去,并辔与他搭讪:
“大爷您从哪儿来啊?”
看看我,不理我。
“大爷您这是走亲戚啊?”
还是不理我。
“大爷您老贵姓啊?”
瞅都不瞅我了。
“大爷你这是回娘家吗?”
这回理我了:
“我抽你信吗?”

八
他怒了,老脸通红,须发皆张,一副鸡毛掸子成精要吃人的架势:
“你这小年轻的,没事儿撩拨我老人家干嘛?闲得你蛋疼啊?
瞎打听什么啊?
官差啊你?密探哪你?看我老人家像贼是吗?你倒看看我浑身上下哪儿还能藏东西?敢惹我,信不信我死给你看哪?”
声色俱厉,吓死我了:
“误会……误会了啊大爷。我是纯属仰慕你啊!一看您就是个年高德劭、道貌岸然的高人,小子我不揣寒陋,愿意效张子房学道于黄石公,陪伴您左右,为您牵马、提鞋……”
老头儿上下打量了我一下:
“有病吧,你?”
叱着驴就跑了。
我赶紧策马跟上去:
“大爷,师父,神仙,您等我一下,我要拜你为师啊!”
老头儿回头鄙视的瞅了我一眼,说:
“我感谢你八辈祖宗啊!
我看起来像几百岁的人哈?
老子我今年才三十三好吧?
笑话谁呢你?”
气鼓鼓的骑驴前行,再也不跟我说话了。
九
我跟在后面,紧赶慢赶的追。
结果赶上一个硬弯儿,等拐过去,老头儿不见了。
骑马的居然把骑驴的跟丢了!
眼看红日西坠,天已向晚。
路边一个鸡毛小店,推门进去,就一间房,一溜儿大通铺。
大通铺上空空荡荡,只歪着一个客人,正是那个老头儿,头底下枕着鹿皮口袋,正假装睡觉呢。
我安顿好马匹,从店主人那儿沽了一坛白酒,拍开泥封,酒香四溢。
老头儿面墙而卧,闻见酒香,肩膀稍微抖了一抖,有戏!
我找了两个椰瓢,把酒分好,满屋的酒香缭绕:
“神仙大爷,整一口啊?还有烧鸡下酒您不忌荤腥吧?”
老头儿噌的一声坐了起来:
“不忌不忌不忌……”
端起酒就喝,抄起肉就啃,片刻就吃成个醉饱,一胡子的酒渍油腻:
“什么三荤五厌哪五荤三厌哪,那是和尚道士的事儿,跟我老人家不相干哪,呵呵……你这小伙儿人不错,知道体恤老年人嘛,嘿嘿……”
“你刚不是说你三十三?”
一坛酒,一只鸡,还有二斤猪头肉,这饭量和牙口,我还真信他只是个三十三岁的白化病人。
这个真假存疑的老头儿呵呵一笑:
“……大爷我也不白蹭你酒肉,如今长夜漫漫,走又走不得,就趁我醉眠之前,给你讲点奇闻吧!”
我问:
“有多奇?”
老头儿说:
“两百年前的事儿,奇不奇?不讲那些大头巾在史书上编的故事,就讲我亲身经历的事儿如何?没错,二百年前我三十三。”

十
老头儿背靠着墙,盘腿坐好:
“那年我确实是三十三。
没错,如今是大唐,大唐之前是大隋,大隋时候南有大陈,大陈之前又有大梁。
宋齐梁陈都是南国的国号,我呢是北国扶风人,姓申名观。
出生那年,北方还是宇文家治下的北周。
十八岁从军,国号已经换成大燕了。
我投在公子瑾麾下,累积军功,从士卒升为裨将,征战了十五年。
三十三岁那年,随军去打梁元帝的荆州。
征战半年,死伤枕藉。
荆州打了下来,主帅命令回兵,凯旋之师却偃旗息鼓,没办法,一场惨胜的糊涂仗,幸存下来的都是些神智不清的僵尸兵。
那天,大军屯在江陵。
军中无事,我在帐篷里闷头睡了一下午,直到被晚饭的香味叫醒。
我坐起来,清清楚楚的记得刚刚做了梦:
只记得梦里有两个青衣人,对我说了几句莫名其妙的话:
“吕走天年,人向住,寿不千。”
奇怪,诡秘,压抑,心脏砰砰跳,不好受。
梦里应该还有其他事儿,只是想不起来了。
我帐前的亲兵是个精细人,见我冲着食案上的酒肉发呆,就知道有事儿。
我跟他说:
“做梦做得没食欲啊!一点都不饿,嘿嘿。真有这好事儿,大军的粮草都省了,一到饭点就睡觉呗,睡饱了就吃饱了……”
那个亲兵说:
“嘿嘿,爷,那我这种成天睡不够的,会不会撑得消化不良啊?”
十一
那个亲兵陪着我,到江陵城里找了个算命的解梦。
算命的这个人也奇怪,挺大的人不留胡子,说起话来也不阴不阳的:
“你呀,当兵的命,到此为止了;当官的命,也到此为止了。
亲兵说:
“他做梦,关我啥事儿啊?”
算命的说:
“本来也没你啥事儿——说的都是他。”
我说:
“这个命也没了,那个命也没了,那我还能活吗?”
算命的说:
“你只要把这两条命丢了,剩下的命就会好好的……”
我抬杠:“那我要是就不丢呢?”
“那样啊,你就啥命也没了。”
我问他:
“那我这梦你还没给解哪,先紧着吓唬人哪?”
那人笑笑:
“你看啊……
梦里的隐语是“吕走天年,人向住,寿不千”。“吕走”就是“回”字,“人向住”是个“往”字,这意思是要你赶紧回家,可得长生啊!”
长生?
这个词好像块砖头一样,砸中了我的天灵盖,我像被谁开了瓢一样,满脸都是……顿悟!
这梦解得有点胡诌。
但是我本人已经厌烦了这连年的征战,回营之后,就以此为借口,向主帅告了退,准备解甲归田了。
没有跟至交好友告别,甚至连亲兵也没打招呼,我自己带了路条,连夜偷偷离开。
天地之间,除死无大事。
回家之前,我又去了一趟江陵,那个算命的也还在。

十二
卦摊儿前冷冷清清,觅食的麻雀,像会飞的老鼠一样蹿上蹿下。
那种乱世,命还值得算吗?
不是打死别人,就是被别人打死,谁又有得选呢?
我坐下问他:
“官我也辞了,军籍我也退了,明天就回家了。
这“吕走天年,人向住”,好办。
那“寿不千”呢?
怎么得长生?
就这么等着,一年一年的捱吗?”
他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一眼,说:
“你怎么还执迷不悟呢?
我在这尘世等了你三十三年了,你怎么还是没一点长进呢?
你不认得我了吗?”
我仔细想了一想:
“我敢确定,没欠过你钱!”
算命的嘴巴歪了歪,一副瞧不起人的嘴脸:
“切……我说,你听,能不能听懂,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啊!”
十三
算命的说:
“你啊,如今是申观,昨天是申将军。
但三十三年前的你,叫薛君胄,家住梓潼。
没错,那是你的前世。
你前世好仙道,在鹤鸣山下买地,筑了三间草堂,房前屋后遍栽花木、山泉巉岩竹影扶疏。
你遍访丹书,服石嚼柏,日诵黄庭百页,夜焚异香一屋。
你穿宽袍,戴峨冠,效古人竹林抚琴、月下长啸,那啸声……把附近的野猫都引来了。
那天正是中秋,你对月独酌,喝得有点上头,开始喝佛骂祖的抱怨:
“我薛君胄恬淡如此,怎么就没有个仙人来渡我,我不配吗?配!配!配!……”
然后,突然双耳之间爆响,滚滚如有雷声,头疼欲裂,倒头欲睡。
耳中的雷声渐渐小了,换成滚滚的车轮声,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
一辆碧油小车,由一匹白马拉着,从你的左耳出来,直接开到了枕头上。
车上跳下两个穿青衣的小童子,有青豆大小,跟你打了个问讯:
“呦呵,先生自在啊!刚才那一嗓子嚎得……真凄厉啊!
我们远在兜玄国深山净室里打坐,都被你这声如裂帛的叫声惊醒了,你老人家……怨气冲天哪?
我们主人说了,既然您这么叶公好龙,那就跟我们回兜玄国吧?”

十四
薛君胄用睫毛打量了一下他俩:
“嘿嘿,你两位豆芽仙人,没事儿消遣我老先生啊?
你俩儿驾车从我的耳窍而出,想必那个兜玄国是在我耳中喽?
你俩让我同去兜玄国,试问我又如何钻进我自己的耳朵眼儿里去呢?
无稽之谈嘛!”
两个小童笑了:
“你老人家还真是没有仙根哪,居然在这种没品的事情上纠结。
我兜玄国幅员万里,又怎么会在你的耳蜗之内?
如若不信,跟来看看嘛!”
薛君胄摇头:
“不去,不去。你们二位身不满寸,如两颗豆子相似,那匹马有颗枣大?
如此推测,你举国上下的人物,岂不都是些小小的耳虫?
不去不去……”
两位童子怒了:
“说谁是虫子啊?你才是虫子呢,朝生暮死昏昏聩聩的玩意儿!
你这无知的架势,居然把我的道心都气歪了,没办法,去也得去,不去也由不得你了,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仙境,强过你在这儿醉生梦死……”
说完,身形爆长,一把抓起薛君胄。
老薛一通嚎:
“来人哪,绑票啊!邪教组织啊!我……不是,你们好像没办法把我塞进我自己的耳朵里吧?嘿嘿……”
童子说:
“早跟你说了,我兜玄国幅员万里,怎么会在你的耳中?
只是,进进出出,总需要个孔窍才好,既然你的耳朵不让用,就用我的吧!”
说完,一个童子提起薛君胄,往另一个童子耳中一塞……就给塞了进去。
十五
薛君胄蒙蒙昧昧,转瞬而至福地。
睁眼一看,晴天朗日,山川壮丽,花木扶疏,鸟飞鱼跃,万类霜天竞自由,别是一派异国风光。
两个童子,拖着他跳上一朵祥云,一路拉拉扯扯,带他来到一间大殿之上。
大殿富丽堂皇,远非尘世可比。
高台之上一具銮驾,端坐着一位王者,披云霞而戴虹霓,垂翠幔而升玉阶。
四个彩衣侍者,分持青红皂白四色玉圭。
两个童子收敛起来,低声吩咐:
“这是我兜玄国的主宰,玄真伯,赶紧叩拜……”
薛君胄畏上,麻利儿的就给跪了。
大殿上闪出一个侍者,宣读敕文:
“肇分太素,国既有亿。尔沦下土,贱卑万品,聿臻于如此,实由冥合,况尔清乃躬诚,叶于真宰,大官厚爵,俾宜享之,可为主箓大夫。”
薛君胄不知如何应对,一个童子用手使劲儿拧他:
“快特么谢恩哪,你现在工作有了,护照也有了啊……”

十六
薛君胄被安排做主箓大夫,但其实无事可做,因为他……不识字。
兜玄国的字,又小又怪,不光是认不得,想学也看不清。
薛君胄闲来无事,每天在班上听人汇报,随口吩咐。
开始他还煞有介事,后来发现自己是自作多情啦,不管他怎么吩咐,下面人该干啥还干啥……
他就是团空气啊!
憋着坏恶搞了几次,胡乱吩咐,下属也只是交头接耳的怪笑两声,丝毫没出乱子。
他明白了,自己就是个酸菜鱼,又酸又菜又多余啊。
心也灰了,意也懒了,班儿也敢翘了,事儿也不管了。
闲极无聊,登楼远眺,无限惆怅。
拿了笔胡图乱画,顺手诌了几行字:
风软景和煦,异香馥林塘。
登高一长望,信美非吾乡。
正独自感慨,被两个童子进来撞见,劈手抢了过去,一看就怒了:
“我去!
你就是个没有根器的糊涂蛋哪!
凭空而得仙箓,不知珍惜也就算了,还在这儿长吁短叹的思乡。
琼瑶仙宫你呆着腻得慌,就爱你那个蚂蚁窝啊?
你忘了当初了吗?
当初是谁在蚂蚁窝的那儿长吁短叹、深夜浪叫,把我们兄弟恶心过去的?
行吧,既然薛先生觉得在这儿受了慢待,那咱干嘛还要强留呢?
回去吧你!”
十七
云程杳杳,瞬息而至。
薛君胄一身蔽衣,又回到旧居处。
山还是旧山,树还是老树,但小溪已经改道,草堂已经坍塌了。
走下山,访四邻,都目瞪口呆的一脸懵逼:
“还以为你让狼叼走了呢,薛先生……你这些年,是去要饭了吗?”
兜玄国几个月,人间已经过了近十年。
之后又过了几年,薛君胄因病而亡。
薛君胄死了,才转生为你,申观申将军。
如今你在这个尘世,又历经了三十三年了。
我这么说,你能跟上吗?”
算命的一脸疲惫的说。

十八
我跟他说:
“绕是绕了点,但还没被绕糊涂。
你的意思是,我前世叫薛君胄,到过仙界叫兜玄国,因为不合群儿,又被遣返了,是吧?
后来他没了,才又有了我,对吧?
那……你又是谁呢?
怎么可能知道的那么清楚?
即便能占卜,又怎么会清楚彼时彼地的每个细节?
你不会就是……”
“没错,”算命的说,“我的前世就是那两个青衣童子中的一个……”
“哪一个?”
“负责来回塞你的那一个。”
“那……你一个仙人又转得什么世啊?也思凡了吗?”
算命的撇撇嘴:
“我懒得理你。
就是你上次被遣返,走得太急,没给你带齐术后的口服药……
上次是你非嚷嚷着找仙人来渡你,结果真到了仙界,发现你这个人还真是叶公好龙,俗骨未褪尽,所以只好把你送回来。
但是走得急,忘了一样东西:
本来位列仙班是可以长生的,你一个被贬之人自然不能长生,但是按规定,谪仙也可以有千年的寿命。
这个符箓……”
说着,他从口中扯出一条红缎带,上面是泥金的符咒:
“……这个符啊,忘了给你别在后背上了。
等我拿了符箓追过来,薛君胄已经死了,你申观申将军也已经三十三了。
所以……我现在给你别后背上吧,也算交差了啊……这跑得我上气不接下气的。”
说完,红光一闪,符箓化进了我的身体。
那个算命的随即变成一个童子,然后就不见了啊。”
老头儿这么说,说得口渴了,又灌了半瓢白酒。
十九
我听得津津有味,都特么饿了,问他:
“那您老人家……”
老头儿拍拍肚皮,呵呵一笑:
“我老人家,在世上已经浪了二百年了。
真是活腻了啊!
草木荣枯,生老病死,兴亡迭代,黄河改道都见过几次了,也算是见识了沧海桑田了……
你不信?那我也没办法啊!
这个鹿皮口袋里……”
他解开口袋,掏出一沓字纸:
“这两百年来,有些大事我都记在上面,都是亲眼得见,绝非道听途说……感兴趣我择两条给你念念?”
我说:“那感情好,求之不得啊……”
他念了两条宫帷密事,果然是闻所未闻、骇人听闻、三观震裂啊……
再后来,我还想听,结果老头儿睡着了。
我把那些字纸拿到灯下看,密密麻麻的像蚂蚁一样的小字,一个也不认识。
再一会儿,灯油没了。
我偷偷的把字纸藏了两页在怀里,也睡着了。
第二天天一亮,一摸铺上,老头儿没了。
我跳起来问店家,店家说:
“公子,昨晚上你喝多了吧?
太吓人了,我也不敢说话。
你对着墙上的那张年画,溜溜的白话了一晚上啊……那可真是熬到了油尽灯枯啊。
我也不敢劝,你就那么坐着,一愣就是半天啊!
末了还把我家那张年画撕了,揣怀里了,你看这……这……”
我往怀里一摸,还真是张画,打开一看,胖娃娃抱大鱼……
但是,五叔,我再一摸,怀里还有两张纸,对着门口的天光一看,密密麻麻的尽是不认识的蚂蚁字,就是昨晚上我藏起来的那两页“仙书”啊……
然后我也蒙了,说:
“画坏了不要紧,我买了,灯油钱我一并还你。就是你得先告诉我,昨晚上那个老头儿往哪个方向走的,啥时候……”
店家一脸懵逼、活见鬼了似的:
“哪有老头儿啊,公子,我这间小店,整晚上就你一个客人哪。”
五叔,你说是不是很神异?”王佐说。

二十
刺史大人王沐,听得有点如醉如痴,一时反应不过来:
“你小子……你先等会儿,我捋一下哈。
你是我侄子王佐,对哈?
你跟我讲,你在杜陵郊野碰上一个老头儿。
老头儿自称叫……申观,说自己活了两百岁了。
然后他给你讲了个故事,说他在三十三岁上,梦见仙人给他留了隐语。
申观找人解梦,算命的又给他讲了个故事,说申观的前世叫……薛君胄,曾经到过仙境兜玄国,还入了仙籍。
后来被贬回人间了,死之后转生成申观。
申观,也就是那个老头儿,得了本属于薛君胄的长寿符,能活一千岁。
后来你跟申观老神仙喝酒,他喝多了,你偷了他两页纸,对不对?”
王佐说:
“对啊,五叔,一点都对啊……”
王刺史目光炯炯,一脸肃穆:
“那……纸呢?”
王佐颤巍巍的从怀里掏出来,奉上去:
“知道五叔大人你好仙道,乃当世的大隐逸,这等仙人至宝,小侄我怎敢私藏?我藏着也没用啊!宝剑烈士、红粉佳人、仙境五叔,绝配啊!”
刺史大人脸上波澜不惊,肚里翻江倒海,仔细地翻看那两页“仙书”,果然都是蚂蚁文:
“嗯,呵呵,你这小子挺孝顺哈,你补缺的事不要着急,就是这……一个月吧,一个月准有消息。”
王佐意兴阑珊,又掏出一张破画:
“哎,我是没有修仙的命啊。
好东西紧着大人、长辈使唤吧。
这张破画应该没什么用吧,我自己留个念想,也算是见过活神仙的证据,沾沾仙气哈!”
刚要收起来,被刺史一把抢过去,据为己有。
“诶,五叔……?”
“小畜生不要吵,好东西要紧着大人使,知道吧?”刺史大人语重心长的开导:
“你小孩儿老老实实去做官,修仙这种清苦事儿,还是大人来做吧哈!”
“不是,五叔,我就算有了官做,这上任之前不还得有一笔调费吗……”
“别废话,别废话啊!小孩儿……怎么还护食啊?五百两,给你五百两!买定……松手,一张画嘛!”

“评书廉颇”,故事多多,欢迎关注。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通知我们,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