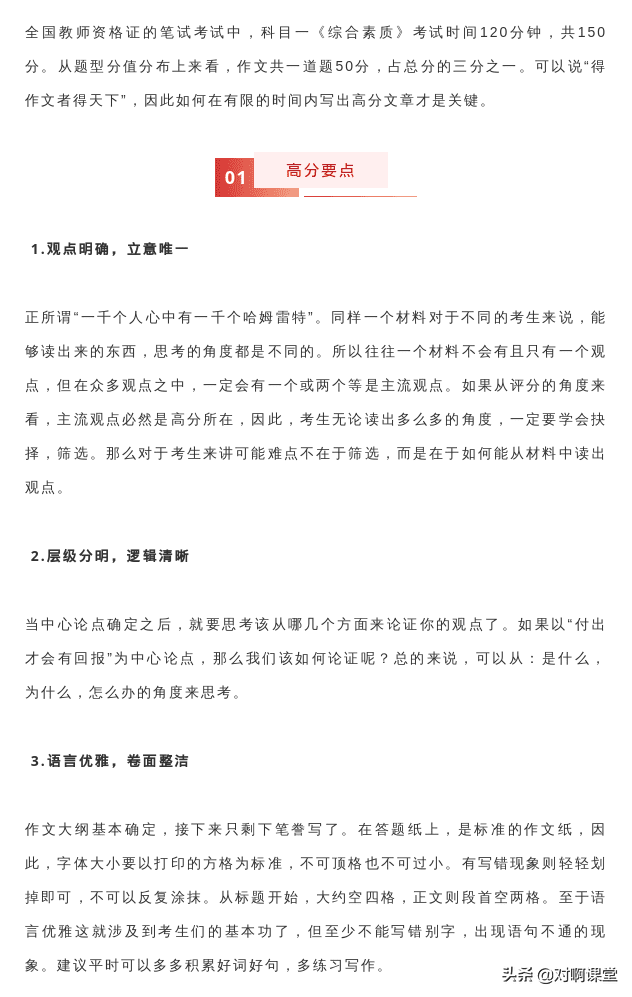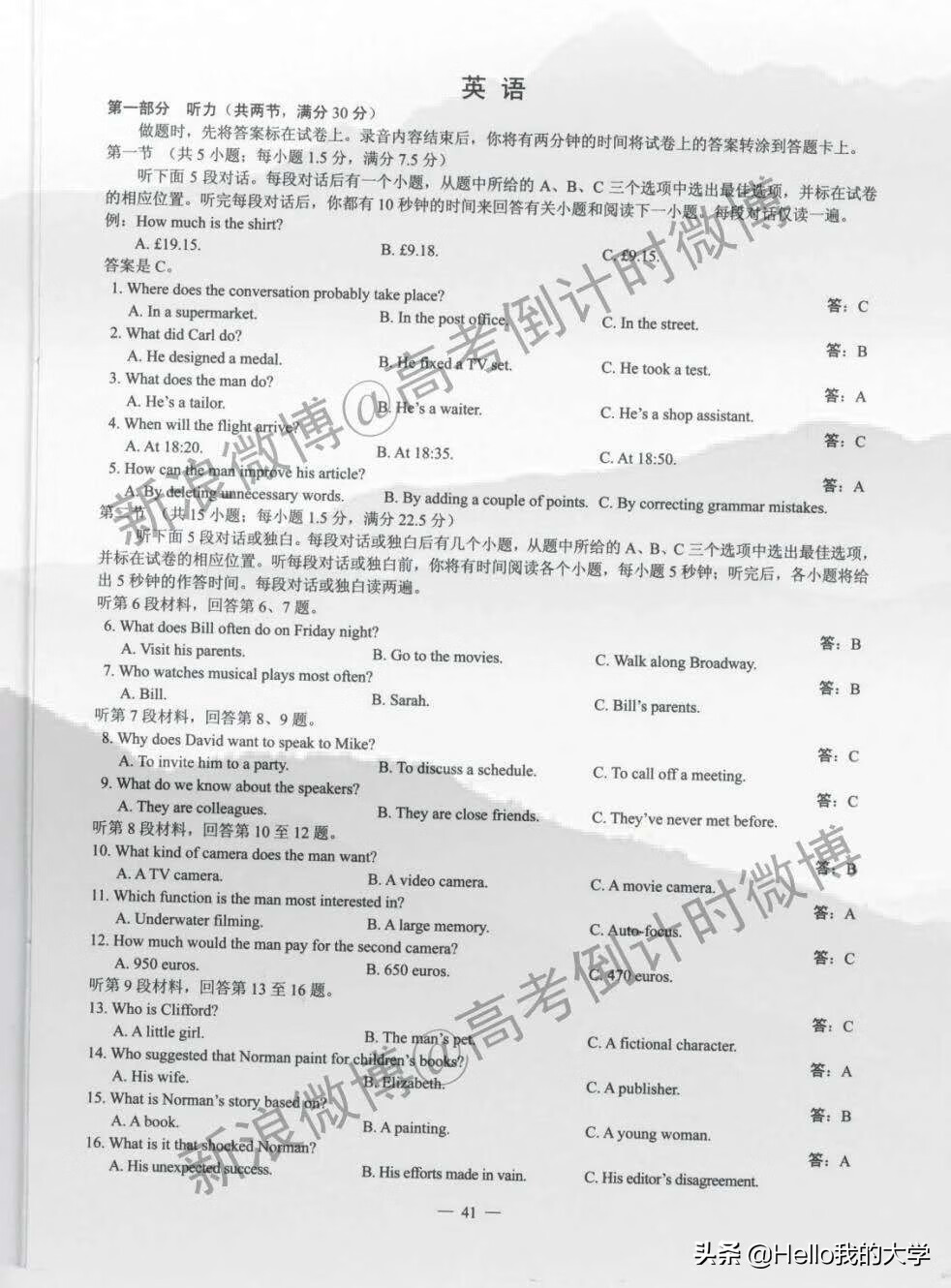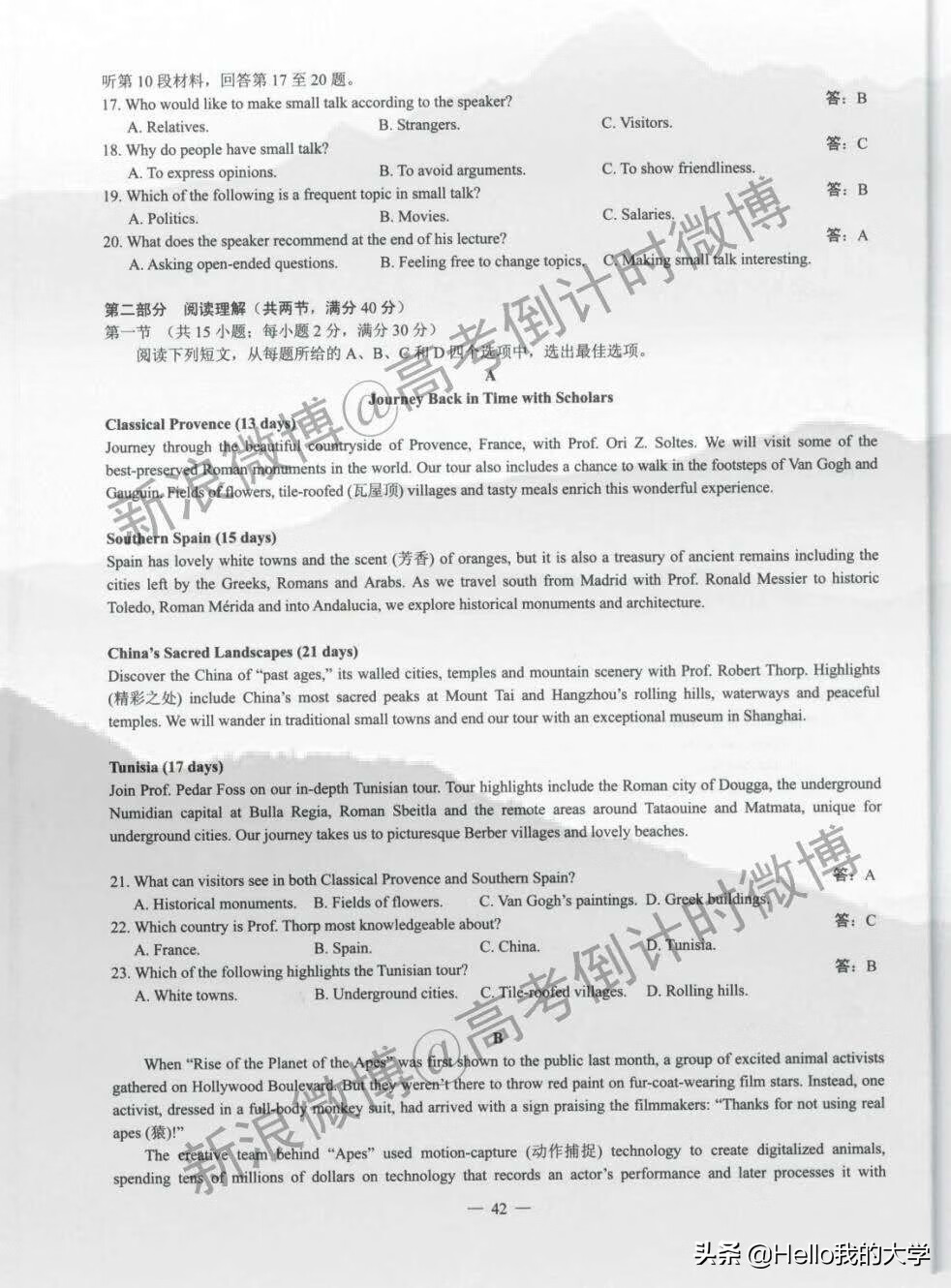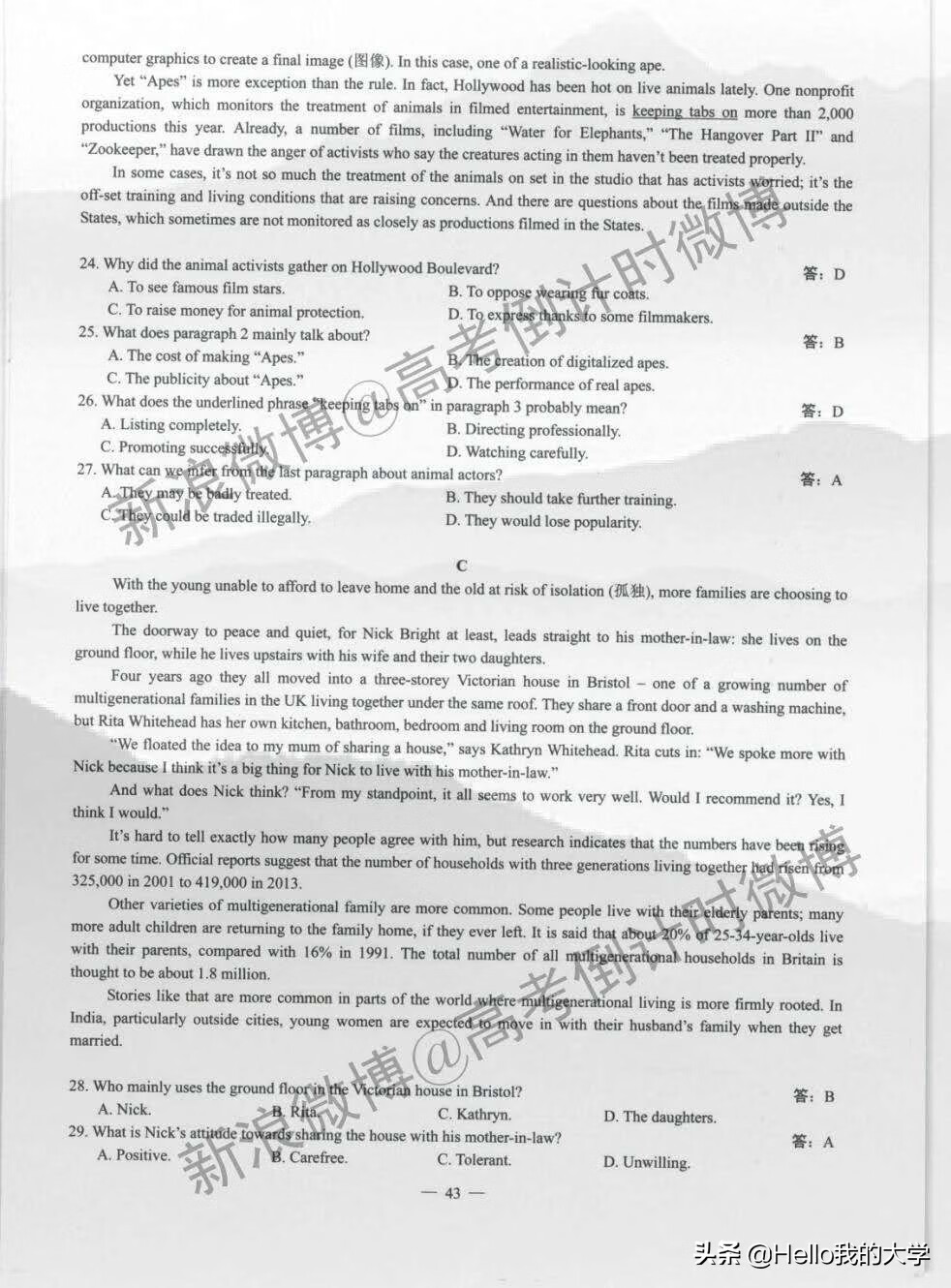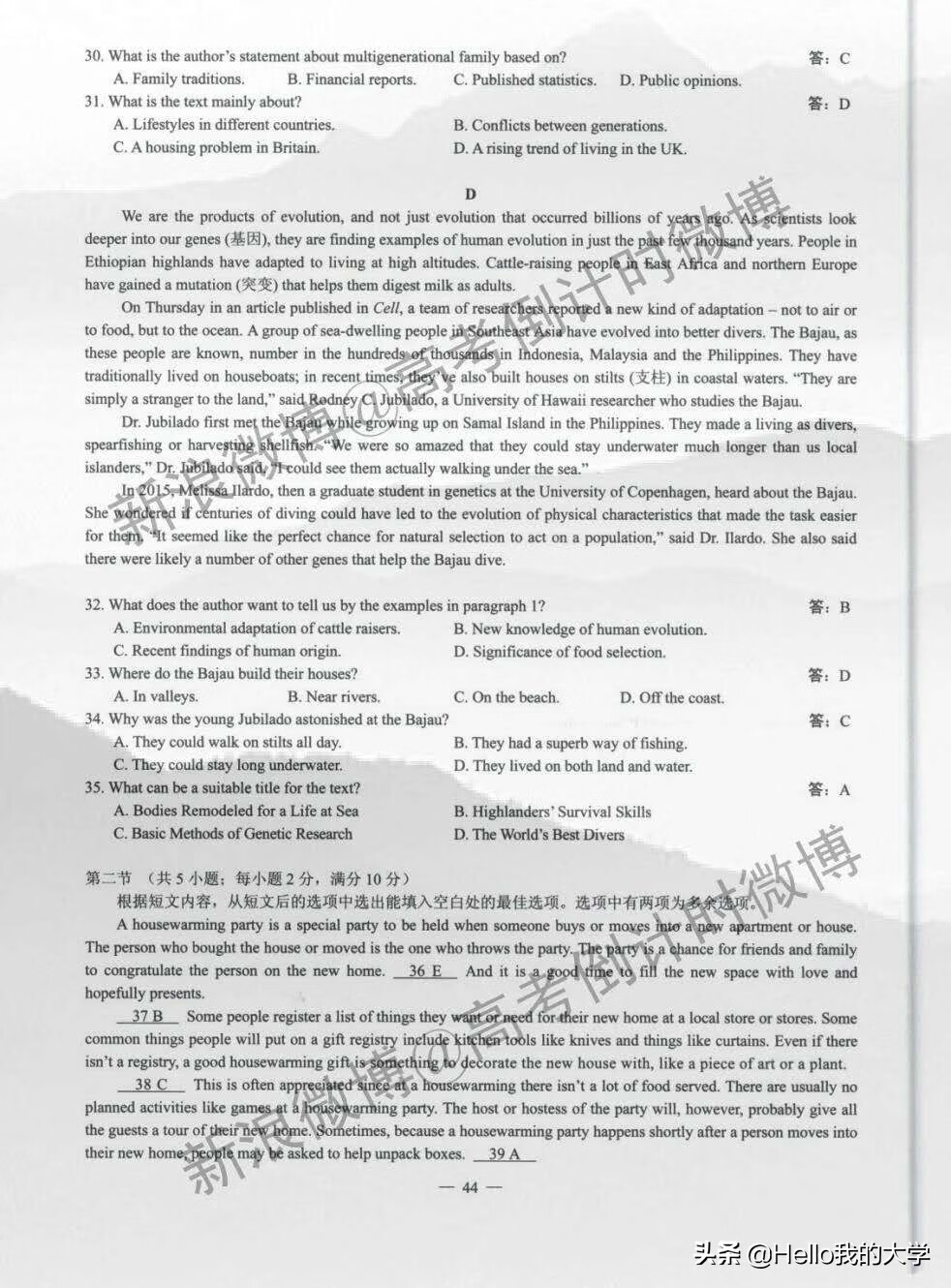.jpg)
本文转自:北大外文学堂
《中国戏曲在法国的翻译与接受(1789—187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一书是我在2012年通过答辩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其中论述的重点是19世纪两位法国汉学家儒莲和大巴赞的戏曲翻译工作,但也涉及了早于他们的一些汉学家——比如马若瑟、雷慕沙、德庇时所做的相关工作,以及这些作品翻译成法文后在法国文学界所引发的兴趣。
关于马若瑟翻译《赵氏孤儿》一事,在我撰写该论文时已经有众多研究。所以我并没有面面俱到地介绍,只是根据论文推进的需要集中论述了几个我的小小发现,作为对前人工作的补充。
以下就是我在这本书中在马若瑟翻译《赵氏孤儿》问题上提供的三个创新的点。
1. 第一个创新点基于我对布吕玛神父书信材料的发现,这些材料使我得以推断布吕玛神父不仅是为杜赫德提供《赵氏孤儿》译本抵达法国这一讯息的人,而且是推动他将此译本收入《中华帝国全志》的人,而布吕玛神父及其周围人对中国戏剧的关注则代表了法国当时对中国戏剧的浓厚兴趣。也就是说,杜赫德将《赵氏孤儿》译本印刷出版这一事件不是一个完全孤立的偶发性事件,而是由当时整个大环境促成的。[见《中国戏曲在法国的翻译与接受(1789—1870)》(以下简称《中》)第一章第一节“一、布吕玛神父与《赵氏孤儿》出版的可能关联”“二、布吕玛有关中国戏曲的引述及其内涵”,《中》第10-16页]
2. 第二个创新点基于我对耶稣会戏剧教学传统、马若瑟本人经历及其致傅尔蒙书信的考察,这些材料让我得以分析并推断马若瑟翻译《赵氏孤儿》的直接目的是以此译本为语言材料,帮助傅尔蒙学习中文,并促使他进而认识到《汉语札记》的价值。(见《中》第二章第二节“一、马若瑟的《汉语札记》与其《赵氏孤儿》译本的关联”“二、耶稣会对戏剧的看法与马若瑟的汉语教学”,《中》第53-58页)
3. 第三个创新点基于我对马若瑟译本与《赵氏孤儿》中文文本的详细比对、对儒莲《赵氏孤儿》初译本手稿及儒莲对马若瑟译本评价在不同时期演变的考察。我发现马若瑟译本并没有如一般所认为的那样摒弃剧中所有曲文,而他对曲文的取舍也证明他不是因为能力不足,而是根据他当时的需求选择了他的翻译策略。后人对于马若瑟的误解部分地来自儒莲的评价,但儒莲的这些话背后有压低马若瑟来凸显自身汉学成就的意图,所以不应被简单地全盘接受,而应当加以分析。(见《中》第二章第三节“从节译到全译的转变——‘观念’或‘能力’”,《中》第61-71页)
这三个点都在新材料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分析和看法,尝试衔接上前人对马若瑟翻译《赵氏孤儿》这一事件叙述中的一些断裂。由此,马若瑟为何选择节译《赵氏孤儿》,又为何将译本提供给傅尔蒙,而原本寄给傅尔蒙的译本又如何会被杜赫德得知,并收入《中华帝国全志》,并最终在法国引发一系列回响,这整个过程或许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勾勒。

……儒莲的戏曲翻译活动始于1829年前后。这是他进入汉学领域的初始阶段。而其早期译作不仅数量较多,且为随读随译,显然有语言学习的背景。虽不难想象作为通俗文学的戏曲小说较之儒家经典更宜作为中文入门读物,但儒莲当时的选择是否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与考虑呢?本节将通过对儒莲《赵氏孤儿》早期手稿的分析作进一步探讨。
一、 马若瑟的《汉语札记》与其《赵氏孤儿》译本的关联
马若瑟是法国耶稣会传教士。1698年与白晋等人一同来到中国,被指派在江西教区。期间曾被召往北京工作过两年。1724年雍正禁教之后,他与其他传教士一同被逐往广州。1733年,清廷再次驱逐传教士,马若瑟又从广州迁往澳门,最终于1736年在澳门逝世。在众多耶稣会传教士中,马若瑟的重要性并非来自显赫的地位或传教上的功绩,而主要源于他在汉语研究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据龙伯格研究,马若瑟来华后,为了研究中国语言文字的奥秘,“把大部分甚至差不多全部时间都用在了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学上”,甚至将传教工作“全扔给了当地的助手”。在其所写的《〈经传议论〉自序》中,马若瑟曾这样记述他来华后学习中文的情况:
瑟于十三经、廿一史,先儒传集,百家杂书,无所不购,废食忘寝,诵读不辍,已十余年矣。今须发交白,老之冉冉将至而不知之,果何为哉?有能度吾之心者,必知其故也。
马若瑟的用心当然并不在于中国语言文字本身,而在于如何更好地说服中国人接受基督教。基于其索隐派观点,马若瑟认为中国的典籍中隐含着基督降临的预言,如果能从中文中挖掘出这些信息,必然会对中国的传教事业有极大的推动。不过由于长年潜心苦读,他的中文程度在耶稣会士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马若瑟撰写的《汉语札记》,被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称为“19世纪前欧洲最完美的汉语语法书”。马若瑟翻译的元杂剧《赵氏孤儿》,是18世纪欧洲读到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中国戏曲作品,自从被杜哈德收入《中华帝国全志》后,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迅速被翻译为多种欧洲语言。此外,除《经传议论》外,马若瑟尚有中文著作三种,分别是《六书实义》《儒教实义》和《儒交信》。《六书实义》是一部以《说文解字》的六书分类为基础,阐述索隐派观点的对话体作品。《儒教实义》是一部马若瑟对儒家种种观念及丧葬、祭祀等活动进行基督教化阐释的著作。《儒交信》则是一部劝人皈依天主教的白话章回体小说,讲述“司马若瑟”如何劝化“李华”入教的故事。以上列举的只是马若瑟的部分著述,但显然已足够证明马若瑟对中国语言文字的掌握程度。
马若瑟的作品中影响最大的当数《汉语札记》与《赵氏孤儿》。这两部著作虽然均得到研究者广泛的关注,但谈及它们之间关联性的却为数寥寥。不过,若从马若瑟晚年在华境遇以及他与傅尔蒙的交往来考察,当不难看到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马若瑟由于其索隐派观点而被教廷视为异端,他的著作因此被禁止发表。此时他已近晚年,又被流放到广东,生活及研究条件很差,因而,当他在1725年通过书信与巴黎东方学家傅尔蒙建立起联系之后,他一直对傅尔蒙寄以厚望,希望能让傅尔蒙接受并认可他的著作,以期通过傅尔蒙让他的著作得到发表和传播。在这样的期待下,他将自己最重要的著作《汉语札记》寄给了傅尔蒙。这份手稿于1730年2月11日抵达巴黎王家图书馆。当时他并不知道,傅尔蒙也写了一本中文语法书,题为《中国官话》,希望藉此证明自己在中文研究上的权威地位。因而他将马若瑟视为竞争对手,不仅未帮助马若瑟出版《汉语札记》,反而故意将其束之高阁。不知就里的马若瑟为了再次敦促傅尔蒙出版《汉语札记》,在1731年寄去了《赵氏孤儿》译本及两封书信。正如鲁进在《马若瑟为什么翻译了〈赵氏孤儿〉》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马若瑟的《赵氏孤儿》译本并不是,至少不主要是出于文学或戏剧的考虑而作,它实际上是为了敦促傅尔蒙出版《汉语札记》而创作的一个副产品。不过,鲁文对于该译本究竟如何起到敦促作用多少有些语焉不详。实际上,细读马若瑟当年的书信,不难得到更为清晰的解答。据书信所述,当时随《赵氏孤儿》译本一同寄往欧洲的是一盒毛笔、40卷《元曲选》和两封致傅尔蒙的信。一封只是简单的寒暄,意在向傅尔蒙介绍两位寄信人的情况。另一封长达九页的信才是正文,信中用相当的篇幅对中国戏曲的艺术形式作了介绍。并介绍《元曲选》说:
……这是一部收录了一百部最优秀元代剧作的文集。不过为了便于你对它的理解,也为了让你有兴趣去阅读它,我尽这七八天的时间做了我所有能做的事。
1. 我简略地为你介绍了所须了解的有关中国戏剧的情况。
2. 我为你翻译了一篇急就之章。
3. 我在中文原书中加注了若干我估计你会需要的说明。
第三条中提到的说明包括以下内容:在《元曲选》第一卷的目录上为全部100个剧目编了序号,在各卷卷首及剧目起始处标注了对应的序号;在《赵氏孤儿》一剧的文本上,用小圆圈对全文进行了断句;在原书上标注了该剧每页的页码,并在译文的相应位置注上了页码;在行与行之间加了一些简单的解释,在页眉处添加了一些注解;等等。如此细致的准备工作充分表明,马若瑟希望傅尔蒙阅读的并不仅仅是《赵氏孤儿》译本,而是这一剧作的中法文对照本。译作也好,马若瑟提供的戏曲概述和中文句读也好,都只是为傅尔蒙进行中文阅读所准备的辅助工具。因为,归根结底,马若瑟所关注的核心乃是他的《汉语札记》。正如他在信中所写:“如果您愿意在上面说到的这部戏,或者另外某篇上练习一下的话,您会觉得我的《札记》对您不是没有用的。”就在这封信中,马若瑟再度强调了《札记》中的知识对于说好汉语和理解中文作品都是必不可少的,并向傅尔蒙保证,对于他的上述论断,“您只需读一部我三四年前寄给您的戏剧或小说就会信服的”。这就是说:翻译是一种语言练习,《赵氏孤儿》译本是他提供的一个样本和范例。而让傅尔蒙通过对照阅读,进而以翻译为练习进入中文学习,同时了解和认识到《札记》的价值,这才是马若瑟真正关注的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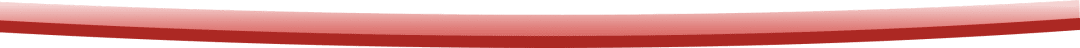
事实上,马若瑟信中所推荐的这一语言学习方法与《汉语札记》所传达的观念是一脉相承的。《汉语札记》共包含三个部分,导言部分是对中文的语音语调汉字等的概述。正文部分将中文分为口头语体和书面语体,分别进行了词法和句法的总结和举例。值得注意的是,马若瑟将口头语体的部分放在了前面,而他用以佐证的文本材料正是戏曲与小说。
在“口语及通俗语体”的导论中马若瑟这样写道:
中国的语言,不论是存留在古书中的,还是应用于日常生活的,都有着它恰如其分的独特的美。对此,绝大多数的传教士都没有予以充分的关注。因而,他们中的少数人,且不说写作,甚至都不能大致正确地说这种语言。那么,既然我现在着手来阐述汉语的独特的气质及其内在的美感,并且将第一部分限于对这种高雅方言(译者注:指官话)的探讨——例如那些出身高贵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所说的那种语言——那么,我认为合宜的做法是首先指出我用以归纳总结出下文这些结论的某些作品;不过,有必要提到的只是其中最重要的那些。这些作品一言以蔽之,就是戏剧,和某些叫做小说的短小文章。首先要提到的是《元人百种》,这部文集收录了一百种戏剧作品,他们最初出版于元代,每篇都不超过四至五场。
可见马若瑟对于通俗语体的总结,并非来自日常生活,而源于口语体的文学经典,因为在他看来,编写这部语言教程的目的在于让法国读者学到中国“上流社会”的口语表达方式。正因如此,在他所选的语料和范本中,《元人百种》处在一个特殊的地位上。综合起来看,导论中的语言学习观,正文中选用的例句,让傅尔蒙借翻译《元曲选》来进行中文学习的建议,与他以经典文本,尤其是戏剧文本为典范,开展语言学习的基本观点都是一致的。
二、 耶稣会对戏剧的看法与马若瑟的汉语教学观
马若瑟的这种观念可以上溯到耶稣会的教学观与戏剧观。作为一个建立于16世纪的以对抗宗教改革为目标的教会组织,耶稣会对于教育非常重视,把教育视为争取青年、巩固天主教会影响的主要手段,因而其教育事业发展相当繁荣。1761—1762年法国议会下令关闭耶稣会学校时,竟致使全国将近80%的男子中学被关闭,可见耶稣会在当时欧洲中等教育领域影响面之大。在教育上,耶稣会有两方面举措非常突出。其一是对于古典文化教育的重视,其二就是戏剧教育:
耶稣会把戏剧作为一种教育手段系统地纳入到学校的教育中,同时也借助它进行牧灵工作,为天主教信仰赢得更多的信众。戏剧也因此受到特别推崇。
在耶稣会学校对戏剧的重视与支持下,校园戏剧非常兴盛。
它(译者注:指耶稣会戏剧)的作者是杰出的教师或有经验的作家,它的演员是来自这个国家里一流家族里的年轻人、学修辞学或是哲学的中学生,它的观众是那些在宫廷或是城市里的高雅人群:高级教士、亲王甚至国王……所有欧洲主要的城市里都有他们(指耶稣会)的学校和剧场。
尽管教会在很长时间内对戏剧所持的态度都是否定的,有关戏剧利弊问题的争论在耶稣会内部也时有发生,但就整体而言,耶稣会认为戏剧的问题并非来自其本身,而在于人们对它的利用正当与否。如果善加利用,戏剧也可以成为道德教化的利器。他们对戏剧的宽容及鼓励,以及在教育中对戏剧的运用,除了出于对戏剧所具备的道德教化作用的重视外,也因为这种艺术形式非常有助于学生学习古典语言及修辞:
文字的学习藉此得到了一种强烈的鼓舞,要令年轻人熟知拉丁语所有的奥秘,很难有比这更好的方法了。
因而,对耶稣会而言,“戏剧不仅仅是一种娱乐,而是一套真正的机制,是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了解到耶稣会的戏剧观及其将戏剧与古典语文教学相结合的传统,再看马若瑟的《汉语札记》与《赵氏孤儿》译本,对于其推崇《元曲选》,视戏曲翻译为语言学习辅助手段等想法也就不难理解了。
作者简介:
李声凤,北京大学法语系文学学士、硕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曾任教于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法语所,现为上海教育出版社编辑。已出版的著作有:《在时代震荡的缝隙中生长——越剧改革与越剧独特审美的形成(1938—1958)》(专著,2019)、《中国戏曲在法国的翻译与接受(1789—1870)》(专著,2015)、《舞台下的身影——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上海越剧观众访谈录》(编著,2015)、《蒙田随笔全集》(合译,2011)、《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西文汉学珍本提要》(参编,2009)、《尹小芳艺术人生》(参编,2008)、《侯麦:爱情、偶然性和表述的游戏》(译著,2006)。另在各类期刊发表有论文及译文若干。目前主要关注领域为中法文化交流和现当代戏曲。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通知我们,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