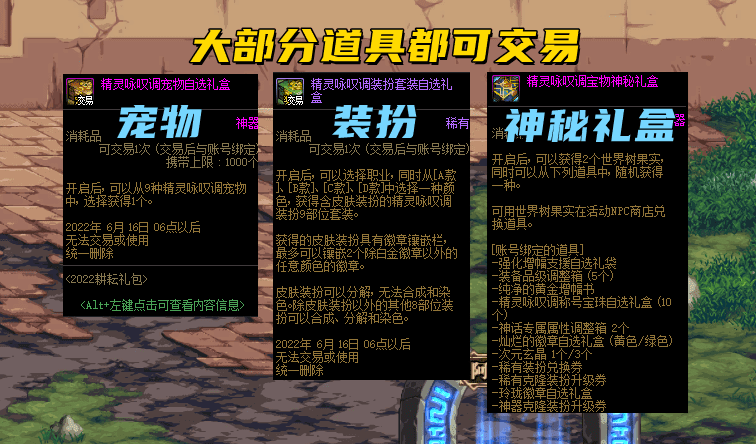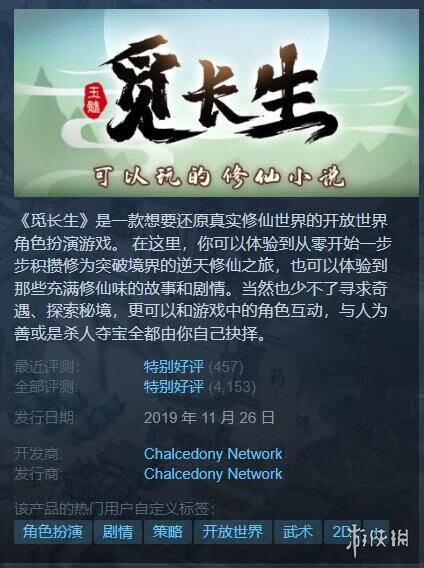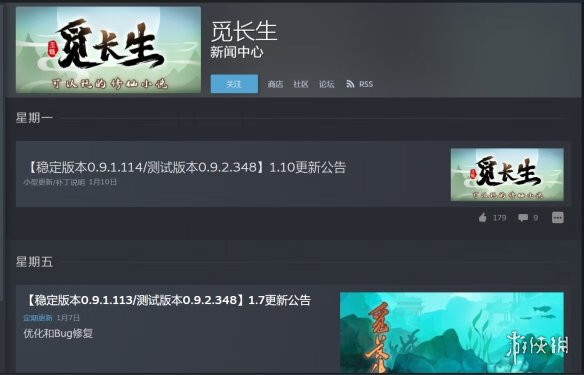.jpg)

老家人管自己的父亲叫大大。
有一回,大大给我买了一本看图识字的小画书,彩色的插图,配有醒目的黑色方块字,还有拼音字母。至今,我依然很记得,那本散发着淡淡墨香的薄薄的画书里,人物,鸟兽,花木,果蔬,都是生活中常见的物什,林林总总,栩栩如生的模样,鲜活,生动,也绚丽,也热闹,总归是极好的。
我伏在大大宽厚而温暖的怀里,跟着他看图识字。大大指着书画里戴眼镜的男子,教我读“爸爸”两个字下面的拼音字母,并解释“爸爸”就是大大的意思。我很不解,为什么读“爸爸”,而不读“大大”呢。他告诉我,大大是方言,爸爸是官称。我越发不解。不过,倒是觉得“爸爸”这个叫法,新鲜而洋气,叫“大大”多土气啊。吃晚饭的时候,母亲催我喊父亲吃饭,我顺口喊了句“爸爸,吃饭喽”。兄妹们听见了,哄笑出声来。七嘴八舌的话里,分明是嘲讽,甚至还有点厌恶的意思,让我很恨地羞愧了好一阵子。
隐约听说,我的祖父母,共生养了11个孩子,仅存活下4个。我大大行10,祖父担心这个小儿子再生意外,便取了个乳名十成,寓意是十拿九稳,定能成活的意思。我大大果真命大,不仅磕磕绊绊地存活了下来,竟然还考上了沭阳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贤官亭小学教书,成了家族中唯一“吃公家饭”的人,着实让目不识丁的祖父,颇感荣耀和得意了一番。这个乳名,或许,还有功成名就的隐喻吧。
大约小学三年级,我随大大转学到离家十几里地的八庙小学。当时,大大在八庙小学当校长。平日里,一周回家一次,很是孤单,就把我带到身边,爷俩做个伴。那时候,在农村,在我的老家大口村,没有谁比我们家更关心星期天了。在大口村,人们更关心中秋,年初一,二十四节气。星期,是一件遥远的事情。在大口村,却因为我的大大,这个小小的村落的人们触摸到星期天的模样了。
星期六的下午,一放完学,大大就推出那辆破旧的永久牌自行车,把我抱坐在大扛上,急急地骑回家。这个时候,大大的情绪是高涨的,脸上洋溢着微红的醉意。有时,会低下头和我说说话,有时呢,嘬嘴吹着口哨,断断续续,拼接成熟悉的调子。自行车在田间小路上疾驶,两旁,是庄稼地,田垄纵横,葱郁葳蕤,野花星星点点,开得恣肆。阳光下,植物的气息在风中流荡。风软软凉凉地吹过来,一会儿软,一会儿凉,究竟是软的多。过了不久,风声,鸟鸣,蛙声,还有大大粗重的喘息,在我的耳畔渐渐隐去。
醒来时,锅屋的煤油灯已经亮起来了。二姐和三姐围着我笑,二姐用嫌弃的表情帮我擦去嘴角的口水,还装作呕吐的样子。母亲的手擀面已经切好了,正在灶台前忙碌,父亲坐在小木凳上,往灶膛里添柴火,俩人一递一句地说着话。灯光在屋子里流淌,温暖,明亮,饭菜的香味在空气里弥漫。
祖父欸着房门,抽着旱烟,笑眯眯地追着我们嬉闹的身影,不时断喝,跑跌倒。祖母呢,似乎有纳不完的鞋底,长长的细线,一针一针穿过鞋底,将满腔缜密的慈爱细细捺实。这样的场景,总让人感觉现世安稳,岁月平定,都在手掌心牢牢握着。多年以后,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样的夜晚,那样的灯光,饭桌前,一家人安静地吃饭,父亲和祖父偶尔对话,轻声慢语,不疾不缓。祖母和母亲好像从来不上桌子的,总是端着饭碗在灶膛边上吃,然后,笑盈盈地看着我们,随时为准备添饭,锅里饭多着呢,下劲吃。
晚饭后,庄邻的小爷爷,三舅爷爷,叔伯,婶娘们陆续来到家里,祖母和我母亲赶紧起身,麻利地收拾饭桌,热情相让大家进屋,递板凳,倒茶水,东家长,西家短地闲谈,不知谁说了什么,咯咯大笑,家里喧闹起来了。
星期天的夜晚,听我大大说书,让我们家成为小村庄热闹的所在。那时候,农村少有欢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平日里,大人们隔三差五的,顶多也就是到六七里地外的乡市赶集,听听淮海锣鼓、扬板琴之类的家乡小戏。偶尔,若能看上一场露天电影,简直是,快活得不像话。
我很记得,大大说的书,大抵是隋唐演义,杨家将,岳飞传之类的典故,比方说,罗少保怒失宝物,程咬金拦路劫财;比方说,杨排风持烧火棍单枪匹马勇救杨宗保;比方说,抗金英雄岳飞精忠报国,诸如此类的故事,都是坊间脍炙人口的传唱流转。那些书,有的,是大大从书店买的,也有的,是他借来的。当时,我已经很认识些字了,曾经偷偷地翻看那些书,尽管认不全,也断不成文,然而,内心里,委实是佩服写书的人,人世间,百转千回的情感牵绊,千军万马的厮杀阵仗,荡气回肠的生死别离,竟然,全浓缩进这薄薄的几页小书,短短的几十个章回里。
大大很是会说书的,庄邻们大多文化不高,有些书面文字难免深奥晦涩,大大就将书面文字表述成口语土话,还模仿唱书人的腔调,咿咿呀呀,有板有眼。多年后,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仿佛就是早几年前的事。煤油灯下,大大捧着书,大声唱诵,狭窄的锅屋里,坐满了人,男人们吸着旱烟,神情淡然,若有所思。女人们呢,大抵是闲不住的,纳鞋底的,拧棉绳的,抱孩子的,个个聚精会神,竖耳细听,入了痴迷。偶尔,有孩子哭闹,抱孩子的女人,赶紧哄孩子禁声,哭闹声反而愈烈,便有人不耐烦,厉声断喝。女人只好抱着孩子,悻然离场。小小的书场,重新安静下来。
有时候,大大说到精彩处,引发满屋的啧啧惊叹,甚至,有人因了某个人物而争执起来。这时候,我的大大便会停顿下来,喝一口茶水,调整下身姿。大家见没了下文,忽然就安静了,眼睛齐刷刷地盯着大大。这个小小的宕延,像极了集市书场的一幕,颇有“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意思。这个时候,我的母亲,通常会停下手里的活,投去嗔怪的一瞥,会意地浅笑了。院子里,有风从泡桐树梢掠过,簌簌响。墙根的某一处,有小虫子在叫,唧唧,唧唧,唧唧。不远处,三五点萤火,飘摇不定,忽然就不见了。
不知过了多久,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家里逐渐冷清了下来,甚至是,整个大口村,也日渐落寞了。早些年,我的祖父母相继离世,兄姊们也陆续成了家。再过些年,大约在我当兵的次年,大大光荣退休了。那段时间,大大频繁给我写信,鼓励我在部队成长进步。给大大回的第一封信,我颇费了一番踌躇,称呼大大呢,还是爸爸呢,感觉都不对味,末了,折中了一下,感觉称“父亲”较为妥帖。
大大的信,时长时短,叙说家里近况,遇到的人和事,字里行间,五味杂陈。有欣慰,有茫然,有隐隐的失望和释然,也有琐碎的幸福和满足。而今,谁还稀罕听我说书了?个个地,天天抱着电视机过,除了吃饭睡觉,恨不能把自己塞进那小电匣子里去。而今,是年轻人的天下了,村上的年轻人,外出上学的上学,打工的打工,经商的经商,风风火火,来了去,走了回,腰里别着BP机,手里拿着大哥大,滴滴,滴滴,滴滴,响个不停,个个都很忙碌,忙得脚不沾地,张牙舞爪的,自以为很不凡了。记忆中,那个严肃寡言的父亲,开始变得碎碎叨叨的,简直像个老小孩。总归是,大大年岁大了,现世的有些事,他是看不准,也看不透了。
2000年的母亲节,康乃馨的芬芳正浓。偏偏,这一天,我们的母亲,却狠心抛下我们,离开了人世间。天妒贤淑。母亲的突然故去,让父亲一夜之间衰老了许多,他独自一人,蜷缩着身子,蹲在院子里的板车上,神情呆滞,面对前来致哀的亲友,不停地重复一句话,天塌了,天,塌了!然后,老泪潸然,泣不成声。我望着大大,心痛至极,眼泪止不住地流,那一刻,我真切地体会到,凄惶的意思。
处理完母亲的后事,兄妹们商量安排父亲日后的生活。大大执意自己单过,一日三餐,简单弄点吃食,我还是能对付的。其实,我们知道,没有了母亲,父亲肯定不好将就。记忆里,我们的母亲,从来是不肯让父亲干家务活的。在母亲的眼里,她的丈夫,天生就是个读书人,读书人怎么能干妇道人家的粗活。想起当年,我们的母亲,毅然决然嫁给他,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俊朗,儒雅,有点羞涩,专心致志地读着书,母亲一眼就欢喜进心里去了。凭了这份欢喜,让我们的母亲,无论面对今后怎样的艰难岁月,怎样的荣辱兴衰,她都一一承受了。
那个年代,物质上,当然是贫乏的,她也曾为柴米犯过愁,忍受过旁人的轻侮,然而,我们的母亲,从来没有后悔过。她生养了6个孩子,粮食不足,吃红薯干,喝开水,把仅有的玉米面饼子,分给祖父母和我们。吃西瓜,红壤子给老人,剩下的给我们,她用刀削去瓜外皮,吃青色的瓜皮,说真甜,甜到心里了。我将信将疑,咬了一口,微苦的瓜皮没有一点甜味,回头便吐了。母亲笑着骂了我一句。其实,在她的眼里,家庭和睦,老人康健,儿女安好,还有她欢喜的丈夫,一家人相伴相守,再大的贫困,磨难,和这一切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这也算是她人生最大的如意了。
母亲走后,大大的生活,全然乱了方寸,像是茫茫大海上,一条失去方向的船只,漫无目的地游弋,孤单,无助,茫然。子欲孝,而亲不待,多年以后,对于大大当时的处境,我和兄姊们一直心怀愧疚,深深自责。那时候,我们都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有各种各样,忙的借口。尽管,隔三差五的,也会回到大口村,买点熟食,果蔬,衣裤,鞋袜,看望大大。大多时间,老屋是上了锁的。从庄邻伯婶的口中得知,大大不是赶集去了,就是打牌去了。
赶集,打牌,成了大大晚年消磨时光的好去处,好法子。然而,他宁可去赶集,打牌,也不会去叨扰他的儿女。有时候,碰巧,大大躺在院子里的藤椅上睡着了,旁边,放着木凳子,一本书倒伏着,老花镜的一只腿缠了厚厚的胶布,茶杯,是我当兵时用过的,杯体上残留的部队番号,已经驳落模糊了。黄昏的余辉,有些颓败,透过泡桐树茂密的叶子,散落到大大的身上,稀落花白的头上,长满胡茬子的脸上,皱巴巴的旧衣裤上。当年,那个俊朗,儒雅,意气风发的青年,那个让我的母亲一眼就喜欢进心里的男人,如今,疲倦,邋遢,萎顿。望着熟睡的大大,这个养育我四十多年的老头儿,我的眼泪,倏忽一下,就流了下来。
今年的母亲节,是我们的母亲过世20周年,明年,是我们的大大过世10周年。前些天,老家叔伯兄弟的孙子大婚,邀我们回去吃喜酒,顺道,回了一趟老宅子。其实,老宅子已经不存在了,早些年前,被规划征用了。还好,地基尚在,废墟上,依稀能记得院子的模样,锅屋,过道,堂屋,还有水缸,泡桐树的位置。还好,老宅子门前的那口老井还在,不知被谁用木板盖上了。
院子西边的竹林,荒废了,遗留下的几株,枯枝黄叶,寂寂地立着,有风轻轻地掠过,无力,飘摇。立在老屋的废墟上,静静地,打量着眼前的一切,熟悉而陌生,一时间,便恍惚了。
院子里的泡桐树,依然挺拔硕大,枝繁叶茂,阳光在院子里升腾,大大躺在藤椅上,戴着老花镜,安静地看书,我的母亲,把簸箕端在膝上,费力地勾着头,捡米里的小虫子。一只老猫,蜷缩着慵懒的身子,伏在母亲的脚下,打盹。午后的阳光很好,明亮,温暖,祥和,我的母亲,朝我大大看了一眼,不知说了什么,俩个人,轻轻笑了。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通知我们,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